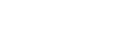0

判斷一個間接轉讓交易是否需要在中國征稅,核心內容就是判斷該交易的境外股權架構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雖然7號公告列舉了“合理商業目的”判斷的七大要素,但很多要素的適用都缺乏具體的指引。比如,7號公告未明確股權或資產的“主要”價值來源于中國應稅財產或投資的量化標準(實務中普遍認為“主要”應指超過75%或者至少超過50%),也未表明該“價值”應如何確定,比如是按照賬面價值或是評估價值。
對于合理商業目的的實務判斷,具有境外上市、境外融資等重要功能的境外上市架構也可能被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最為常見的情況,是中國企業搭建紅籌架構在境外成功上市。這類型架構在實務中常被視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因此轉讓這些架構中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權并不需要在中國交稅。但是,如果紅籌架構搭建完成并在境外完成融資后未成功在境外上市,那么前述架構的“合理商業目的”的認定就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轉讓未上市的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權是否應在中國交稅就具有不確定性。
如果被轉讓的境外控股公司設立于典型的避稅地,不具備特征明顯的商業實質,并且除了持有中國公司股權外不持有其他資產,那么這種類型的間接轉讓交易很有可能被中國主管稅務機關根據7號公告重新調整為直接轉讓中國公司股權的交易,進而需要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
實務中較為常見的一種股權架構是通過離岸公司持有中國境內商業房地產。這類架構中的離岸公司一般設立在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BVI)、中國香港等低稅率或零稅率的國家/地區,因此轉讓離岸公司股權在當地不用交稅或所得稅負很低。除間接持有中國境內房地產外,離岸公司一般沒有其他資產,因而在進行股權價值評估時,其絕大部分的股權價值均來自于中國境內的不動產。對于轉讓此類離岸公司的交易,實務中在境內繳納企業所得稅的可能性很大。
題主可以參考:境外公司間接轉讓境內公司股權案例分析
一、案例簡介
(一)交易基本情況
2018年8月,中國臺灣地區A公司(以下簡稱“臺灣地區A公司”)及其下屬英屬維爾京群島(BVI)B公司(以下簡稱“B公司”)與中國境內合肥Y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Y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合同,B公司將其持有的中國香港地區C公司(直接轉讓標的,以下簡稱“香港地區C公司”)49%的股權轉讓給Y公司,從而間接轉讓了中國境內合肥Z公司(間接轉讓標的,以下簡稱“Z公司”)100%的股權。
1.轉讓方基本情況
B公司是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設立并存續的公司,是臺灣地區A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無實際經營。A公司是中國臺灣地區上市公司,是一家筆記本電腦代工企業,主要經營筆記本電腦、液晶電視、手機及各種電子零件的制造及銷售業務。
2.受讓方基本情況
合肥Y公司是中國境內居民企業,成立于2018年,注冊資本14.43億元。其由北京E公司和合肥F公司共同投資設立,從事股權投資、管理及信息咨詢業務,其實際控制人為合肥F公司,合肥市國資委100%控股合肥F公司。
受讓方股權架構見圖3。
3.標的企業基本情況
合肥Z公司是中國境內居民企業,成立于2011年,是香港地區C公司投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2.65億美元,主要從事計算機硬件、軟件系統及配套零部件、辦公自動化設備的研發和生產。
4.中間層企業基本情況
香港地區C公司是根據中國香港地區法律設立并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由香港地區X公司和B公司共同投資設立,成立于2011年,注冊資本3億美元,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及貿易相關業務。其下屬臺灣地區D公司(分支機構,非獨立法人)主要為集團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其中,香港地區X公司為中國香港地區上市公司。
(三)企業備案情況
臺灣地區A公司及其下屬B公司因集團整體發展策略,決定于2018年轉讓香港地區C公司49%的股權,從而間接轉讓了合肥Z公司100%股權。期間,轉讓方企業代表前往主管稅務機關咨詢相關涉稅事宜,認為轉讓標的為中國香港地區公司股權,可不在中國繳納所得稅。
主管稅務機關認真對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判定,立即將上述情況納入跟蹤管理,并及時向上級稅務機關匯報相關情況。受讓方合肥Y公司作為政府投資方代表,也前往稅務機關進行情況說明和政策咨詢。2018年8月,臺灣地區A公司和B公司委托中國臺灣地區某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代理人與主管稅務機關取得聯系,就該股權轉讓事宜進行再次溝通。主管稅務機關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以下簡稱“7號公告”)相關要求請企業提交資料,并就該案件進行審核分析。
二、分析審核情況
(一)關于合理商業目的的因素分析
1.根據7號公告第五條和第六條進行分析
根據7號公告第五條,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相關的整體安排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不確認其為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非居民企業在公開市場買入并賣出同一上市境外企業股權取得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在非居民企業直接持有并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情況下,按照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的規定,該項財產轉讓所得在中國可以免予繳納企業所得稅。
此次股權轉讓不是在公開市場進行的交易,且如果由B公司直接轉讓合肥Z公司的股權,該項財產轉讓所得在中國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此次交易不適用本條的豁免條款。
根據7號公告第六條的規定,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應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交易雙方的股權關系符合相關規定;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后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次間接轉讓交易情況下的相同或類似間接轉讓交易,其中國所得稅負擔不會減少;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系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股權轉讓方B公司與股權受讓方合肥Y公司不具有相互持股的關聯關系,且股權受讓方并未以該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系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因此,不能直接認定該交易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2.根據7號公告第四條進行分析 7號公告下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境內公司股權案例分析
(二)初步結論
綜上分析,主管稅務機關認為該間接股權轉讓的整體安排應直接認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重新定性該間接轉讓交易,確認為直接轉讓合肥Z公司股權的交易,對轉讓所得征收非居民企業所得稅。該項股權轉讓存在通過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間接轉讓了中國居民企業股權。
三、處理方案
(一)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的確定
根據7號公告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源泉扣繳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7年第37號,以下簡稱“37號公告”)等文件相關規定,B公司有來自于中國境內的股權轉讓所得,是本次股權轉讓的納稅義務人。
根據7號公告第八條的規定,合肥Y公司作為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對股權轉讓方直接負有支付相關款項義務的單位,應為該間接股權轉讓的扣繳義務人。
(二)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根據7號公告第十五條的規定,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股權轉讓合同或協議生效,且境外企業完成股權變更之日,根據納稅人提交的資料,此次股權變更之日為2018年8月31日,因此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2018年8月31日。
(三)稅款計算
主管稅務機關要求企業補充提供初始投資簽署的協議,包括香港地區C公司、B公司、臺灣地區A公司2017年度財務報表等資料。按照37號公告等相關文件規定,股權轉讓收入減除股權凈值后的余額為股權轉讓所得應納稅所得額。
1.股權轉讓收入
(1)轉讓對價
合同約定B公司向合肥Y公司轉讓股份最終對價為25736.8萬美元,按2018年8月31日匯率折合人民幣為17.56億元。
(2)調減項目
香港地區C公司資產中應歸屬于臺灣地區D公司的部分為5490.14萬美元,按49%持股比例計算,應調減2690.17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84億元。據此,確認轉讓收入為15.72億元。
2.股權轉讓成本
設立合肥Z公司時,香港地區C公司共投入資本26500萬美元,其中49%來源于B公司,因此B公司股權轉讓成本為26500萬美元×49%=1298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為8.83億元。
3.股權轉讓應納稅所得額和應納稅額
股權轉讓應納稅所得額為15.72億元-8.83億元=6.89億元,按10%的稅率計算扣繳非居民企業所得稅為6890萬元。
四、案例啟示
(一)結合實際判定合理商業目的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和7號公告,股權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是判定間接轉讓在中國境內繳稅的決定性因素。在7號公告出臺之前,合理商業目的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主觀的判斷,更多依賴于稅務人員的經驗進行判定,容易導致操作標準不統一,給納稅人帶來不確定性。7號公告明確了直接認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直接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等情形。除此之外,還詳細列舉了若干條款綜合分析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使合理商業目的的判定更具有操作性和針對性。但稅企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思考角度不同等因素,對于同一交易稅企之間的判定結果往往不同。在實踐中,稅務機關在對間接轉讓進行判定時,不能僅從稅收角度出發,應多方位思考其商業因素,從而作出相對合理公正的判斷。
(二)完善稅源監控機制
間接轉讓行為的稅收監管難點在于股權轉讓方和被直接轉讓的企業均在境外,部分受讓方也在境外。對于稅務機關來說,很難掌握和了解其交易信息。本案受讓方是合肥市企業,在其對外支付款項時主管稅務機關順藤摸瓜,最終掌握其交易情況并據此征稅。如果股權受讓方也在境外,稅務機關就無法依靠傳統手段掌握交易信息。這就要求稅務人員對國際稅收工作有高度的敏感性,關注報紙網絡上的信息報道及企業架構變化。此外,稅務機關應加強對來華直接投資的非居民企業的日常監管,關注居民企業股權結構、分配股息紅利等情況,開展稅源分析,及時發現跨境稅源管理風險。
對于合理商業目的的實務判斷,具有境外上市、境外融資等重要功能的境外上市架構也可能被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最為常見的情況,是中國企業搭建紅籌架構在境外成功上市。這類型架構在實務中常被視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因此轉讓這些架構中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權并不需要在中國交稅。但是,如果紅籌架構搭建完成并在境外完成融資后未成功在境外上市,那么前述架構的“合理商業目的”的認定就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轉讓未上市的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權是否應在中國交稅就具有不確定性。
如果被轉讓的境外控股公司設立于典型的避稅地,不具備特征明顯的商業實質,并且除了持有中國公司股權外不持有其他資產,那么這種類型的間接轉讓交易很有可能被中國主管稅務機關根據7號公告重新調整為直接轉讓中國公司股權的交易,進而需要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
實務中較為常見的一種股權架構是通過離岸公司持有中國境內商業房地產。這類架構中的離岸公司一般設立在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BVI)、中國香港等低稅率或零稅率的國家/地區,因此轉讓離岸公司股權在當地不用交稅或所得稅負很低。除間接持有中國境內房地產外,離岸公司一般沒有其他資產,因而在進行股權價值評估時,其絕大部分的股權價值均來自于中國境內的不動產。對于轉讓此類離岸公司的交易,實務中在境內繳納企業所得稅的可能性很大。
題主可以參考:境外公司間接轉讓境內公司股權案例分析
一、案例簡介
(一)交易基本情況
2018年8月,中國臺灣地區A公司(以下簡稱“臺灣地區A公司”)及其下屬英屬維爾京群島(BVI)B公司(以下簡稱“B公司”)與中國境內合肥Y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Y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合同,B公司將其持有的中國香港地區C公司(直接轉讓標的,以下簡稱“香港地區C公司”)49%的股權轉讓給Y公司,從而間接轉讓了中國境內合肥Z公司(間接轉讓標的,以下簡稱“Z公司”)100%的股權。
1.轉讓方基本情況
B公司是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設立并存續的公司,是臺灣地區A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無實際經營。A公司是中國臺灣地區上市公司,是一家筆記本電腦代工企業,主要經營筆記本電腦、液晶電視、手機及各種電子零件的制造及銷售業務。
2.受讓方基本情況
合肥Y公司是中國境內居民企業,成立于2018年,注冊資本14.43億元。其由北京E公司和合肥F公司共同投資設立,從事股權投資、管理及信息咨詢業務,其實際控制人為合肥F公司,合肥市國資委100%控股合肥F公司。
受讓方股權架構見圖3。
3.標的企業基本情況
合肥Z公司是中國境內居民企業,成立于2011年,是香港地區C公司投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2.65億美元,主要從事計算機硬件、軟件系統及配套零部件、辦公自動化設備的研發和生產。
4.中間層企業基本情況
香港地區C公司是根據中國香港地區法律設立并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由香港地區X公司和B公司共同投資設立,成立于2011年,注冊資本3億美元,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及貿易相關業務。其下屬臺灣地區D公司(分支機構,非獨立法人)主要為集團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其中,香港地區X公司為中國香港地區上市公司。
(三)企業備案情況
臺灣地區A公司及其下屬B公司因集團整體發展策略,決定于2018年轉讓香港地區C公司49%的股權,從而間接轉讓了合肥Z公司100%股權。期間,轉讓方企業代表前往主管稅務機關咨詢相關涉稅事宜,認為轉讓標的為中國香港地區公司股權,可不在中國繳納所得稅。
主管稅務機關認真對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判定,立即將上述情況納入跟蹤管理,并及時向上級稅務機關匯報相關情況。受讓方合肥Y公司作為政府投資方代表,也前往稅務機關進行情況說明和政策咨詢。2018年8月,臺灣地區A公司和B公司委托中國臺灣地區某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代理人與主管稅務機關取得聯系,就該股權轉讓事宜進行再次溝通。主管稅務機關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以下簡稱“7號公告”)相關要求請企業提交資料,并就該案件進行審核分析。
二、分析審核情況
(一)關于合理商業目的的因素分析
1.根據7號公告第五條和第六條進行分析
根據7號公告第五條,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相關的整體安排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不確認其為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非居民企業在公開市場買入并賣出同一上市境外企業股權取得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在非居民企業直接持有并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情況下,按照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的規定,該項財產轉讓所得在中國可以免予繳納企業所得稅。
此次股權轉讓不是在公開市場進行的交易,且如果由B公司直接轉讓合肥Z公司的股權,該項財產轉讓所得在中國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此次交易不適用本條的豁免條款。
根據7號公告第六條的規定,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應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交易雙方的股權關系符合相關規定;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后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次間接轉讓交易情況下的相同或類似間接轉讓交易,其中國所得稅負擔不會減少;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系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股權轉讓方B公司與股權受讓方合肥Y公司不具有相互持股的關聯關系,且股權受讓方并未以該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系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因此,不能直接認定該交易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2.根據7號公告第四條進行分析 7號公告下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境內公司股權案例分析
(二)初步結論
綜上分析,主管稅務機關認為該間接股權轉讓的整體安排應直接認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重新定性該間接轉讓交易,確認為直接轉讓合肥Z公司股權的交易,對轉讓所得征收非居民企業所得稅。該項股權轉讓存在通過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間接轉讓了中國居民企業股權。
三、處理方案
(一)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的確定
根據7號公告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源泉扣繳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7年第37號,以下簡稱“37號公告”)等文件相關規定,B公司有來自于中國境內的股權轉讓所得,是本次股權轉讓的納稅義務人。
根據7號公告第八條的規定,合肥Y公司作為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對股權轉讓方直接負有支付相關款項義務的單位,應為該間接股權轉讓的扣繳義務人。
(二)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根據7號公告第十五條的規定,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股權轉讓合同或協議生效,且境外企業完成股權變更之日,根據納稅人提交的資料,此次股權變更之日為2018年8月31日,因此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2018年8月31日。
(三)稅款計算
主管稅務機關要求企業補充提供初始投資簽署的協議,包括香港地區C公司、B公司、臺灣地區A公司2017年度財務報表等資料。按照37號公告等相關文件規定,股權轉讓收入減除股權凈值后的余額為股權轉讓所得應納稅所得額。
1.股權轉讓收入
(1)轉讓對價
合同約定B公司向合肥Y公司轉讓股份最終對價為25736.8萬美元,按2018年8月31日匯率折合人民幣為17.56億元。
(2)調減項目
香港地區C公司資產中應歸屬于臺灣地區D公司的部分為5490.14萬美元,按49%持股比例計算,應調減2690.17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84億元。據此,確認轉讓收入為15.72億元。
2.股權轉讓成本
設立合肥Z公司時,香港地區C公司共投入資本26500萬美元,其中49%來源于B公司,因此B公司股權轉讓成本為26500萬美元×49%=1298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為8.83億元。
3.股權轉讓應納稅所得額和應納稅額
股權轉讓應納稅所得額為15.72億元-8.83億元=6.89億元,按10%的稅率計算扣繳非居民企業所得稅為6890萬元。
四、案例啟示
(一)結合實際判定合理商業目的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和7號公告,股權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是判定間接轉讓在中國境內繳稅的決定性因素。在7號公告出臺之前,合理商業目的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主觀的判斷,更多依賴于稅務人員的經驗進行判定,容易導致操作標準不統一,給納稅人帶來不確定性。7號公告明確了直接認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直接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等情形。除此之外,還詳細列舉了若干條款綜合分析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使合理商業目的的判定更具有操作性和針對性。但稅企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思考角度不同等因素,對于同一交易稅企之間的判定結果往往不同。在實踐中,稅務機關在對間接轉讓進行判定時,不能僅從稅收角度出發,應多方位思考其商業因素,從而作出相對合理公正的判斷。
(二)完善稅源監控機制
間接轉讓行為的稅收監管難點在于股權轉讓方和被直接轉讓的企業均在境外,部分受讓方也在境外。對于稅務機關來說,很難掌握和了解其交易信息。本案受讓方是合肥市企業,在其對外支付款項時主管稅務機關順藤摸瓜,最終掌握其交易情況并據此征稅。如果股權受讓方也在境外,稅務機關就無法依靠傳統手段掌握交易信息。這就要求稅務人員對國際稅收工作有高度的敏感性,關注報紙網絡上的信息報道及企業架構變化。此外,稅務機關應加強對來華直接投資的非居民企業的日常監管,關注居民企業股權結構、分配股息紅利等情況,開展稅源分析,及時發現跨境稅源管理風險。